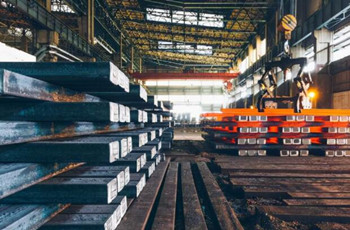从“中国文化西来说”到力证“中国文化自成体系”
如果没有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三门峡市的召开。或许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
从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挖下第一铲,发现与磨光了的石器共存的彩陶,并命名为仰韶文化起,到经过山西夏县西阴村、北京西郊周口店、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历城城子崖、陕西宝鸡斗鸡台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的重大考古挖掘和发现,我们可以感知“中国文化西来说”对第一代考古人深深的刺激,也可以感知他们为证明“中国文化自成体系”的不懈努力,更能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后几代考古人对考古技术与考古认知的追求。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一百年,站在一部更加完整、系统、科学的中华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提民族复兴,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考古学,重新思考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首先应该还原一个完整的中国考古学探索史,应该在李济等前辈奠定的基础上追求一个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更加科学、理性、系统、立体的考古学。
因此,我们将展现百年考古历史上的三张面孔,他们的面孔,浓缩了中国的考古史。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李长需
第一张面孔:安特生
拉开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提出刺痛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召开,再一次将我们的目光拉向一个外国人,即被称为“仰韶之父”的瑞典人安特生。他在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他自己,也成为“仰韶之父”。
一百年前的1921年10月,安特生带着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5位中国学者,以及布莱克、师坦斯基等两位外籍博士,来到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
安特生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因为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赫文·斯定发现了楼兰古城,而把考察的热情和探险的目光投向中国。1914年5月,他接受北洋政府的邀请,就任中国农商部矿政司顾问。
10月27日,安特生指挥团队开始发掘。这一发掘,被他曾经的中国助手、中国考古界后来的重要学者李济,称为是“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
就连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也在其1922年4月1日的日记中,称赞“他(安特生)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
安特生的工作,配得上李济和胡适的称赞。他是个认真的人,整天待在工地上指导发掘,绝不疏忽任何一个发掘的细节,有时候甚至在工地上过夜,为的是随时解决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学者,则从他身上获得了近代考古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和方法,改变了中国之前只有金石学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状况。
安特生的挖掘工作持续了36天,直到12月1日才结束。他们一共开挖了17个发掘点,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发掘结束后,安特生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竖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以示保护。
在仰韶村发掘完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对所带回来的实物进行“会诊”,发现这些实物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特征,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鉴定、比较、分辨和论证,按遗存深度进行逐层分析,结果一致认定了安特生的判断: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遗存中也多有彩陶,所以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将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从文献记载的夏商时期,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承上启下的重要支点。
1923年,安特生在发表的《中华之远古文化》一文中,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异同,从相近似的彩陶纹饰来看,他认为仰韶文化可能是从中亚地区传播而来的,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彩陶西来说”,也即“中国文化西来说”,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不少本土学者的附和。安特生随后又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相关考古,试图证明他的这种假说。
第二张面孔:李济
开启中国现代考古 力证“中国文化自成体系”
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深深地刺痛了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也更激发了他们通过考古资料重建中国古史的热情。李济,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员。
李济1918年由清华学堂选送留学美国,5年内拿了三个学位:前两年,在克拉克大学拿到了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学位;后三年,拿下哈佛大学人类学的哲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顶着人类学博士的光环,但李济一生主要的事业却是考古学。按照他晚年的说法,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从人类学家转为考古学家”:1926年他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
这一年的10月15日,他和跟随安特生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袁复礼一起,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的资助下,在夏县西阴村开始了首次发掘。
整个发掘工作由李济主持。他们采用“探方法”挖出了八个两米见方的探坑,另有四个探坑因不完整而未编号。李济首创了以X-Y-Z来表明陶片位置的“三点记载法”,还发明了逐件登记标本的“层叠法”,即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次,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发掘工作进行得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33个层位。
“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点线)”等这些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评价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很简单,在60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西阴村的发掘,扩大了安特生仰韶文化分布的版图。
事实上,对于安特生等外国同行在中国的“光荣与梦想”,李济的心情也是极为复杂的:“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这些情形,至少我们希望,不会继续很久。”
的确“不会继续很久”。自1929年起,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李济开始主导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终止。
在殷墟的发掘,不仅出土了大量引起各界关注的甲骨及其刻辞,揭示了甲骨文的奥秘,还发现了大量的建筑遗迹、墓葬、车马坑、陪葬坑,以及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文物,进一步证明了殷墟是商朝末代王都的所在地。
李济曾说过,殷墟发掘是“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连贯起来,做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殷墟的发掘与发现被认为是可以与特洛伊发掘坐实荷马史诗相媲美的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0年,趁着殷墟发掘的间隙,李济又去发掘了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确定并命名了以往不同于仰韶彩陶的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史前文化——龙山文化;次年,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梁思永在洹河南岸高楼庄村北高岗的殷墟发掘中,辨认出仰韶-龙山-殷墟遗存自下而上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即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确定了它们从早到晚的时间序列。
至此,中国自甲骨文记录上溯到史前的历史框架——仰韶、龙山和殷墟大致上贯通了。加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切实地说明了中国从旧石器时代以来遗址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历史相对连续,文化自成系列得到了考古的证明。
安特生的“彩陶西来说”乃至“中国文化西来说”,完全被推翻了。
第三章面孔:苏秉琦
开启考古人才培养“辉县模式” 开创中国考古“苏秉琦时代”
苏秉琦是河北高阳人,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他本想毕业后在北平或老家做历史教师,但没想到在毕业前夕,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知人善任,认为他机敏且稳重,专心且善思,更适宜做研究工作,就把他推荐给了徐旭生任所长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
徐先生看苏秉琦对中国现代考古学“修国史”的任务很着迷,就给他予以重压。同年10月底,让他与何士骥一起前往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沟东区。在这次发掘和研究中,他选择以瓦鬲为切入点和重点,对墓葬和器物逐一分类,还将全部40件瓦鬲分为四种类型。
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系统运用分型分式法,将器物按其形态差别而划分为型、亚型和式别,这也是第一次根据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来判断各单位的相对年代。此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皆以此为范例,形成普遍使用的“型”和“式”的概念,苏秉琦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梁思永和夏鼐为副所长,实际负责所务。其研究人员包括苏秉琦在内只有8个人,加上技术员和技工也才14人,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全部的考古力量。
考古所成立之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员不足,急需培训干部,并扩大研究队伍。为此,考古所于1950年10月组团前往河南辉县开展发掘工作。发掘团由夏鼐任团长,郭宝钧为副团长,苏秉琦为秘书长,该团的任务主要是对团里的四名年轻人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殊进行一对一的田野考古培训。
从1950年冬到1952年春,发掘团先后在辉县的五个地点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结束后编写的《辉县发掘报告》,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它建立了新中国考古的范式。
在发掘和撰写报告的过程中,四位年轻人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后来他们都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为彻底解决国家考古人才短缺问题,北京大学在1952年至1955年间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到了369人。训练班的核心课程是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及实习,教员主要来自辉县发掘团。这批训练班成员日后大多成为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辉县模式”经由他们而深深扎根于中国考古界。
1952年,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中设立考古专业,辉县发掘团的多位成员在北大承担课程。苏秉琦则在北大考古专业创办伊始即兼任专业主任,直至1983年北大考古系成立后才卸任。他在北大的努力,为新中国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辉县模式”经由北大考古也在全国发扬光大。
苏秉琦不仅在考古实践、考古教育上贡献卓著,而且在考古学思想和理论研究上也创立了考古学上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学说和考古学基础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周边地区不断有与中原发展水平相近甚至更为先进的考古发现,这使习惯于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受到挑战,苏秉琦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区系类型的理论。他将中国人口密集地区在万年以内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该理论被认为“找到中国文明起源‘破密’钥匙,发现了分层中华民族的形成道路,论述中国的传统精神”。
他提出的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模式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至今仍是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20世纪90年代,苏秉琦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时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的思想,并认为他的区系理论和国家形成的三个模式能够提供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钥匙。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还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派”这个概念,认为应“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应该作为我们的目标、努力方向,这是中国考古学必由之路”。
苏秉琦的考古学理论被认为,不仅是新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果的原因,而且还将成为以后考古学深化发展的指南:“在尚未出现能够超越或取代‘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新的理论学说以前,中国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时代’。”
扩展阅读
-
- 800米的经济文化巨变 2024-02-18 13:30:56
- 江西铜鼓:加速形成文旅产业发展新格局 2023-11-24 12:39:28
- 陕西:以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2023-10-27 11:28:15
- 以高质量国际传播促进文化传承发展 2023-10-26 10:12:40
- “文博热”带动中国双节假期消费热 2023-10-10 09:08:15
- 瑞士向中国移交5件流失文物 2023-08-25 14:34:59
- 新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