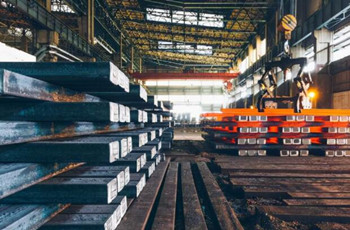美丽中国:心伴海鸥
每逢秋冬到昆明办事或出差,我总会百忙中竭力抽出些许时间直奔森林公园旁的翠湖,去拥抱自然,去见海鸥,去找寻我的心。
清晰地记得,9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丽的红嘴鸥千里迢迢开始飞抵翠湖一带过冬的时日,那时我正在翠湖畔的云南大学就读。每每周末,我和好友都会早早约齐了,急匆匆、欣欣然赶赴翠湖,风雨无阻。
殊不知,偌大的翠湖上空早已成为一个白花花飞舞的世界,透映着自然的清纯,弥漫着森林的芳香。放眼过去,影影绰绰的只见洁白蓬松的海鸥羽毛在明艳的阳光下,划过条条弧线,翩跹而过,闪烁着柔和的银光。红中微黄的一双双可爱爪子轻盈抓逐着人群飞扬起的面包屑。继而,扑腾着翅膀,鸣了天籁之音,欢舞欣喜得如同纯真孩童。暖煦风中,有的海鸥箭一般擒到面包屑,仰空飞食而去;有的敏捷齐扎水面,夺食而欢;有的索性飞落湖岸,寻人觅食,憨态可掬地微颤着清丽的身躯,招人欢,逗人喜,迎人乐……
仿佛置身画中,如梦,似幻。海鸥飞处,洁白在绽放,水花在飞翔,树影婆娑,涟漪依依,欢声荡漾,眼睛应接不暇,心里却依稀地安谧静美,澄澈清纯得如同那冰清玉洁的海鸥。
一天,在翠湖公园围栏外欢腾的人群中,我们见到了一位正小心翼翼恬静地喂着海鸥面包、操贵州口音的女孩,衣着朴实,但却洗得平整白净,衣服表面隐隐粘附着一些斑驳、细碎的棉絮,眼眸明澈,白皙清秀的笑脸,圣洁的,泛着纯洁之光,年龄约莫十二、三岁。
攀谈之余,顺了她的手指,我们终于看到了她的“家”——在翠湖边云南省文联办公大楼前面的平地上,依凭着两棵大树歪歪斜斜地撑起了一个塑料帐篷。帐篷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侧隅的木支架上,女孩的父母正在挥汗忙碌,替一些春城市民进行破旧棉絮的重新加工。
原来,女孩帮父母的间隙,也会偷偷用省下的零钱买些面包给海鸥投喂。女孩边投面包边对我们说:“海鸥和我一样,都是外地来的,乍一看到,特别亲切。喂它们,好像在喂我自己,说不出的温馨,好高兴啊,连空气都是甜的。”
于是,我们眼含热泪,静谧了心绪,于翠绿的森林旁,菁菁自然中,与天使一般的“海鸥”女孩,静静地投喂着我们的海鸥,没有言语,美丽无声,胸中洋溢了爱,充溢着无比的幸福和人格的芬芳。
然而,第二个周末,清晰地记得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早晨,当我们步行穿过云南大学校园,沿着绵延的森林小道,重又赶到那片空地时,即刻惊呆了,面包沉沉坠地。凉风拂面,周围一片静穆,只有缄默孤寂的那两棵参天大树,女孩没了,帐篷不见了。
正当我们惊愣中,旁边不远处一位平日里支画架帮行人画素描肖像的长须老者,站起身,颤巍巍地递给我们一张折叠平整的纸条以及三袋面包,并轻声告诉我们,前一天夜里,有两个无赖竟然戴了口罩揣了凶器闯入女孩家帐篷,威逼着抢走了他们白天弹棉絮挣的血汗钱。
恍若晴天霹雳,仿佛天旋地转,脑海一片空白。俯在翠湖的石栏上,男生哽咽,女生全哭了。
泪眼朦胧中缓缓地打开那纸条,女孩有些歪斜但却娟秀的铅笔小字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好心的哥哥、姐姐,没办法,我们提前走了。在走之前,因为爹爹在流泪,我恳求妈妈把她藏在鞋底的十二元钱中拿给我三元,买了三袋面包,托这爷爷交给你们。请哥哥姐姐以后帮我喂一下海鸥,像我们一样总在漂泊的海鸥。
纸条下方右角较为端庄地署上了她的名字——“侍妮娅”。
一下子,我实在不能自抑,悄然躲到云南大学校园僻静处,心如刺痛,胸虚得紧,泪滑至口唇,涩涩的,苦苦的……
每年,我们还去喂海鸥,只是极少言语,知道女孩至美的心在远方看着我们,看着海鸥,那澄澈如水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海鸥的保护、对海鸥的关爱、对海鸥殷殷的挂牵与眷恋。
看着四周正与海鸥共欢同乐的人们,说真的,我们很欣慰,特甜蜜,煞似森林中弥漫的那丝丝甜润。宛若仙境,这是一个爱的天堂,一个美的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在或者已经开始真诚地用爱心诠释着建设“美丽中国”的行动,见证着纯净甜美的和谐。心美,一切都美。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
学业结束,收拾行装,我们也走了。但我悄悄把自己的心留了下来,留着那片森林旁,留在翠湖,心伴海鸥……
扩展阅读
-
- 美丽中国:请留步,渐渐远去的森林…… 2013-06-03 10:13:23
- 美丽中国:踏雪之恋 2013-02-27 14:15:34
- 美丽中国:圣洁的纳木措 2013-02-22 16:54:13
- 美丽中国:梨花深处是故乡 2013-02-01 11:23:36
- 网络故事:网络新色彩 2012-12-20 17:06:34
- 森林经营给力生态文明美丽中国 2012-12-18 15:17:46
- 新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