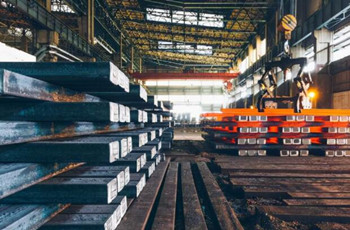世界更平”还是“娱乐更加至死”
“世界更平”还是“娱乐更加至死”
———以《中国达人秀》的网络收视初探社会化媒体的媒介偏向
□田翔
“扁平世界”的收视率神话
在互联网时代,以传统的统计学思维,可能很难接受“34%”——这是《中国达人秀》决赛的节目在上海地区的收视率。
在今天这个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可以作为一个个人走向全球”①的“扁平世界”,人们大多认为像20年前《渴望》那样的收视影响早已一去不复返,大众媒介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多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而是“被拽出来”。②也就是说,媒体的热点及其媒介价值,应该是由媒体参与者(笔者不愿意用“受众”一词,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受众与内容生产者没有明显的鸿沟)的行为所决定,而非传统的大众媒体。
如果说《中国达人秀》决赛34.88%的收视率(峰值超过35%)以及8月份平均15.52%的收视率③(均为上海地区)数据中,覆盖过多的家庭型用户——他们中的家庭主妇并不上网,不属于“扁平世界”;那么,在网络电视平台上的收视数据则应该具备一定的说服力。以PPTV网络电视平台为例④,《中国达人秀》,《快乐男声》等热门节目的收视表现也非常惊人,在今年8月份,达人秀的直播(与电视台同步收看)收视人数占到当天全平台直播收视人数的5%以上,而《快乐男声》的这一数据更达到了12%-20%⑤,这个数据也超过了《快乐男声》在传统电视平台上的毛收视率。
另一个数据更能说明这种收视并非偶然收视或者“看看热闹”。无论是《中国达人秀》,还是《快乐男声》,在PPTV网络电视平台的收视时间几乎都在15分钟以上(《中国达人秀》的收视时间最低5.41分钟,平均在10分钟左右,其中最高的一天为20.71分钟),《快乐男声》尤为明显(均在20分钟以上,最长达到28.72分钟)。“扁平世界”里的“碎片化”传播似乎失去了作用,恰恰相反,他们被电视节目“击中”了,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奉献给了电视台,电视媒体“娱乐至死”的效应仍然存在着。
来源于“技术”的娱乐关注还是来源于“人”
这个现象提醒我们,仅从“扁平世界”的思维方式考察网络传播似乎是不够的——
从传播学角度看,“世界是平的”的观点,与麦克卢汉所预言的状态——“印象和经验相互交换、相互转换……读者就在自己生产新闻,或者他自己就是新闻”⑥颇为相似,它创造的是“没有边缘的多中心”。从媒介即讯息的观点看,互联网带来的这种规则本身也传递了某种信息——一种自由平等隐喻,知识更容易传播,有效信息会被迅疾和无处不在的电子网络筛选出来,政府和机构在传播中的影响被减弱……总而言之,互联网媒介传递着一种鸿沟被减弱的“平”的信息,人们在信息消费乃至工作协作方面都呈现更大“自我”的价值。
但事实却让我们看到,包括《中国达人秀》网络收视在内的不少互联网事件,如“拜小月月”、“凤姐现象”,似乎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平”,还是电视内容本身引起了“娱乐至死”。那么,在这其中,媒介的偏向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为何又没能让世界变“平”呢?笔者倒更愿意从这样几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包括《中国达人秀》在内的网络娱乐消费是否还存在电视时代的影响,即世界会越来越平,只不过人们的行为目前还保留着电视时代的痕迹;
我们对互联网的“媒介即讯息”理解是否过于简单,互联网传递的不仅是“世界是平的”,对互联网技术的理解是否应该看到更多维度;
在研究方法的角度,能否通过一些数据的细节差异分析,去理解用户的行为,从而窥探媒介表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关于“媒介即讯息”,或者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有一种批判显得相对理性,他们认为麦克卢汉研究虽然过少关注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但它的一个重要启示恰恰在于,提醒我们关注“技术产生并采用之后后果如何,带来了什么影响”⑦。事实上,麦克卢汉自己也不同意将其看作“技术决定论”者。笔者的理解是:在麦克卢汉看来,人也是媒介的一部分,比如互联网媒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互联网的技术看作模式的全部,人们在其中制定的游戏规则也是模式的一部分,这可以看作广义的“技术”,而游戏规则形成以后,人们在规则中的行为表现——比如如何转发信息——都是媒介的组成元素,这一切共同影响了“媒介的讯息”。
在电视媒介时代,电视的图像传播和时间线性让人们失去了理性思考的空间,压迫着人们在信息消费的时候失去思考的自由,而宁愿被电视击中,这也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力巨大的原因。⑧
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从电视受众行为的角度,他们面对线性的图像播出,更愿意做一个“沙发里的土豆”,人性先天的惰性与媒介技术特性的结合达成了这种“娱乐至死”;从电视运营者的角度,他们会刻意放大电视的这种媒介特性,将信息碎片化,通过“每个镜头不超过3.5秒”的方式,争夺用户的时间,从而获取其商业价值。这样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把人的因素纳入到媒介模式中,将媒介技术与社会权力结合起来考虑。媒介虽然是一个“场”,却是一个被政治场和经济场所控制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其他场进行着控制。⑨
那么,在互联网呢?如果考虑人的因素——无论是媒介方式的游戏参与者还是规则设计者,它的媒介偏向可能与纯粹的技术考虑得出的结论会有所不同。在这个游戏规则中,受众行为为何会导致娱乐事件的集中关注,娱乐产业运营者又应该如何去影响这个媒介“场”,从而达成其政治经济目的呢?
信息平等还是被迫娱乐:社会化媒介是何隐喻
互联网如今走到了社会化媒体时代,如果说Web1.0的传统互联网还有更显著的大众媒介特征——只不过是文字、图片和电视的非线性阅读,那么,社会化媒体更接近麦克卢汉预言的“神经网络”,信息沿着人与人的心理、兴趣、经验交集传播。如果不考虑人的因素,结论当然是世界变平;然而如果考虑人的因素,互联网可能不是让世界变平,而恰恰可能导致“娱乐更加至死”。
社会化媒体提供了这样一种技术可能:在海量的信息中,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将每个人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筛选出来。与此同时,信息还在被酝酿,舆论还在被发酵,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的下一个传播节点以“观看的理由”。
从这个过程我们就不难发现,技术仅提供了一个人与人对话的平台,在这其中,人和信息的名誉、影响力等都通过其他人的意见、信任而获得⑩。这样的机制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个熟悉的传播学概念——“沉默的螺旋”,由于人与人的意见交流更加容易,这种螺旋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同时,不仅在心理上的这种螺旋被强化了,而且这种心理机制被投射到了技术上——不被“大众”所关注的信息和意见,其转发的可能也被大大减少了。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种反向作用,即越是被反对的意见,越是由于“吵架”而引发话题的迅速发酵,以至于造成整个舆论场的聒噪。
因而,笔者更愿意以另一个维度去区分“沉默的螺旋”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作用——沉默的标准不再是意见是否被认同,而是意见或信息是否足够“出位”、是否更“娱乐”。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化媒介的隐喻,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波兹曼所述的电视媒介的“娱乐至死”效应。(当然,就如前文所述,这其中不仅有技术模式的原因,还有“人”的原因——运营者利用技术模式所做的种种策略,我们会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个问题。)
这种发酵效应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人们从“集体观看”,转变为“异步观看”。在《中国达人秀》和《快乐男声》的网络收视数据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特点。
从这组数据来看,《中国达人秀》从第三周开始,在PPTV平台的点播率开始超过《快乐男声》,其单个节目的站外播放率(从其他网站如社区、微博等链接到本站)也超出一般影视剧节目近50%,而《快乐男声》则没有这个特征——即便我们同样提供了每个选手的单个节目片段。这个数据与笔者前文所列的直播数据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去考察这两档节目的特色就不难解释这个问题:《快乐男声》作为一档传统的选秀娱乐节目,其品牌影响力、直播特色、故事的完整性都符合传统电视节目的特征——即便它符合波兹曼所述的电视的碎片化特征,但它仍然试图依靠赛制的悬念、赛程的完整性(一步步晋级)吸引观众;而《中国达人秀》甚至强调录播——更关注每个选手的单个节目的表现力、选手的争议性以及单个碎片的制作品质。显而易见,后者更符合前文所述制造社会化媒介传播的特点,这种话题性极强的节目形态,在社会化媒介传播中更能体现出“娱乐性”,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被卷入了这个传播场中,即便不喜欢,也帮助这种信息的传播。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达人秀》的网络收视时间普遍低于《快乐男声》。当然,由于《中国达人秀》还是采用了很多电视手段,用户也有对电视媒介的认同惯性,因此《中国达人秀》的收视时间并不如想象的短,用户进入了节目以后,还是会被节目吸引住。可见,关于前文的三个问题,电视习惯惯性只是互联网收视奇迹的一个很小因素,重点在于互联网的媒介倾向决定了一定程度上的娱乐性,从很多细节数据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以广告主的名义:占领时空和挖掘价值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的“媒介即权力”论,无论是模式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本质动机都是基于经济或政治的权利诉求,是为媒介运营者服务,媒介不仅“表达了信息”,而且这种表达因为人的原因是可以控制的,即把人看作技术的一部分,人可以决定技术的发生和发展——这也是理论界所认为的完善和发展麦克卢汉理论的渠道。
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比起报纸媒介对用户空间的占领和电视媒介对用户时间的占领,互联网其实既可以做到对用户时间的占领也能做到对用户空间的占领。前者更具娱乐倾向,而后者更具理性倾向。
如前文所述,目前的这些社会化媒体,如论坛、微博等,更显示出某种娱乐性。笔者认为,为了追求这种娱乐性带来的商业价值,运营者其实更倾向于占领用户时间。以微博为例,运营者通过将信息碎片化,阻止复杂逻辑观点的传播,降低互动的进入门槛(140字谁都会写)。信息量的增加有助于伴随化的形成,从而强化了其对用户时间的占领。
从前文所述的“媒介即权力”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将未来的互联网运营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制定游戏规则(其实就是以政治经济为目的设计新的技术模式),比如微博就是以占领用户时间为经济诉求;另一类是利用游戏规则(其实就是在新技术模式下发挥和放大其媒介倾向,以获得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这种媒介创新与内容形态的创新是同步和交叉的,同一个内容运营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还包括每个用户)甚至会同时针对不同技术模式平台发布内容,其中的诉求实现方式一定也会有所异同。
最简单的遐想就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创造出某种游戏规则(或称为技术模式),使其表达非娱乐化价值倾向。“维基百科”占领用户空间的技术模式设计,其实就有类似倾向。
更重要的是,这种媒介价值与内容价值分层更加明显和二者创新周期的缩短,增加了广告主诉求的难度。如果说在电视时代,广告主对媒介和对内容的诉求基本统一,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技术模式和内容模式的复杂化,广告主有必要理清他们在不同媒介倾向和媒介内容下的诉求,来挖掘用户价值。
例如在《中国达人秀》的决赛环节中,光明牛奶以电视广告的思维,斥巨资投入了插片广告。然而,由于《中国达人秀》在互联网传播更多以内容的角色出现,而非占领时间轴的主角,所以用户在观看插片广告的时候,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价值传播的广告。但由于这批广告与内容的相互植入不足,更多的仅是展示,加之其广告插入点扰乱了节目的正常话题性进展,因为其本身变成了反面话题,引来了微博、SNS社区用户的强烈不满。
由于媒介与内容的分离,在社会化媒介的倾向中,这种展示型广告更多地应该植入在媒介运营者上,通过插入到用户时间轴中产生展示效果;而在内容碎片中应该更多采用植入型广告,并且尽量减少负面话题的可能性,更强调创意、实用信息量和互动性而非展示性。
事实上,互联网更多是一个基础技术平台,提供了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重技术手段。因而,研究互联网媒介的媒介倾向,不能把互联网看成一个单一的媒介,而是多个新媒介模式的集合,在这个集合中媒介倾向可能是多重的,其与内容的关系也将表现出比电视等传统媒介更加明显分离性(电视的媒介倾向基本决定了其媒介内容,而互联网的内容却可以运用于多个不同倾向的媒介)。因而,将权力引入到媒介即讯息的概念中,也将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定量研究,去分析用户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新空间。
注释:
①[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 肖莹莹 郝正非 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9月
②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众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P.88-89
③数据来源:CSM 2010年8月上海地区主要频道节目收视排行(测量仪数据)http://www.csm.com.cn/download/12city/1008/shanghai.html
④关于这两个节目,PPTV均为官方合作伙伴,在宣传推广等资源的投入上几乎相等,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完全排除节目主办方社会推广因素对两节目的影响,因此,本文中的分析更趋向于定性分析,难以达成严格的统计学科学性。
⑤观看人数比更接近于“毛收视率”概念,但又有所区别。即每个观看用户都算作一人,多次收看不重复计,分母为全站当天所有观看直播(不含点播)的人数,数据总和可能超过100%。该数据为全样本统计。
⑥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 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P.428-430
⑦李洁 《传播技术构建共同体——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P.152
⑧同上,P.87-89
⑨韦路 严燕蓉《媒介:讯息还是权力?——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再思考》,《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暨CAC/CCA中华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 2004 年,P.186
⑩Webb,Matt,“On Social Software”,http://interconnected.org/home/2004/04/28/on_social_software
■李洁 《传播技术构建共同体——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P.98-99
■参看 [加]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河道宽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PPTV网络电视)运营总监)
扩展阅读
-
- 光明日报:现实题材影视将持久赢得观众的心 2019-07-01 13:32:34
- 人民日报海外版:网络"恶搞"要有底线 2019-05-06 11:04:17
- 北京青年报:别让“过度娱乐”淹没未成年人 2018-08-27 12:40:49
- 光明日报:影视剧应塑造健康的现代女性形象 2016-09-22 11:56:33
- 四问纸媒深度报道 2016-01-22 11:40:14
- 新华网董事长、总裁田舒斌:应更加重视自律和他律相结合 2016-01-04 11:30:47
- 新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