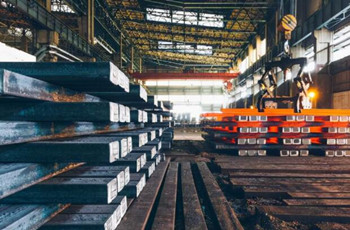媒体应当敢于对公众人物实施监督
● 汤啸天
所谓公众人物,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正式的界定。笔者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的社会成员。例如,政府公职要员、公益组织的领导人、文艺界、体育界、娱乐界的明星以及著名科学家、知名学者、模范人物、重大荣誉称号获得者等。这类社会成员因为担当公务要职或者经常抛头露面,以自己的行为构成了公众形象的一部分,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演变起到了超出一般社会成员的作用和影响。
笼统地说,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成员都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公众人物所处的显赫地位和经常抛头露面,其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社会成员。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公众人物的行为涉及公共利益,应当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应当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督,舆论监督即是其一。
鉴于公众人物的形成与其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不同,学术界又将公众人物分为完全型公众人物、志愿型公众人物、非志愿型公众人物三类。
完全型公众人物,是指因为承担公职、履行公务、接受重大荣誉称号等处于社会关注状态的人。
志愿型公众人物,是指出于其自身的愿望、需求,跻身于社会某一方面的瞩目位置,得到舆论关注并影响舆论的人。
非志愿型公众人物,是指某些人本身不是公众人物,但因某些事件的发生而偶然卷入其中,才成为“公众人物”的。偶然的非志愿型公众人物具有暂时性,随着事件影响的衰减,很快又回到普通人的行列。
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对完全型公众人物、志愿型公众人物的监督。
对公众人物的舆论监督国际上早有先例可循
在世界新闻史上,公众人物的概念起源于美国的萨利文案。据资料记载,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整版的文字广告。文中的内容系批评南部一些地方官员对民权运动的指责、对和平斗争暴力镇压以及其他的非法手段。这版广告指出的问题是真实的,但也存在不少小的、非实质性的事实出入。警官萨利文(Sullivan)指责文章对当地警察局的行动报道是虚假和诽谤性的,要求赔偿50万美元。
案件经州法院一审,萨利文胜诉,纽约时报社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3月9日,联邦法院以9对0票否定了州法院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认为,公共官员(Public Of Ficial)应当接受公众的监督,而新闻媒体在报道公共官员时是很难做到不出一点错误的,这种犯错误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真理需要这种生存空间。
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为了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公共官员起诉新闻媒体诽谤案,不仅要证明普通法要求的有关内容已经发表,给自己造成了损害,而且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上的恶意”(Actual Malice),方有可能胜诉。
美国法学界认为,“纽约时报判例”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原则,在美国确立了一种“新的宪法性的诽谤法”(The New Constitutional Law of Defamation),新闻媒体在报道和评论官员和“公众人物”时被赋予宪法特许权(Constitutional privilege)。对公民批评或评论“公众人士”的言论予以宽容。
联邦最高法院申明的“实际上的恶意”原则,不仅从宪法的高度为新闻媒体批评政府和公职人员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而且对美国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那时起,新闻媒体在诽谤诉讼中就逐渐处于有利和主动的地位。
当然,这一趋势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表现依然具有差异性,但批评公众人物的言论应予宽容的大势已不可动摇。
我国法制建设对舆论监督公众人物也有积极作为
在我国,因为批评公众人物引发诉讼的案件大体有两类,针对完全型公众人物的大多数涉及诽谤罪,针对志愿型公众人物的大多导致名誉权纠纷。
就新闻媒体而言,其非常不愿意牵扯到刑事或者民事诉讼案件中去,急切希望国家法律能够充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也能够为媒体发挥监督作用提供更大的空间。
近年相继发生的所谓“诽谤案”,大多是指责公权力的滥用,当“诽谤者”以“危害社会稳定”为由被采取刑拘、逮捕等强制措施之后,刊发相关稿件的媒体也被累及。
故实际生活中,我国报刊已经很少发表批评公权力的稿件,至多只是略微搞一点“异地监督”。所以,民众更多地采用网上发帖、群发短信等方式表达对官员的批评,报刊充当被告的情形有所减少,而在网上发帖的人被追究诽谤罪的数量明显增加。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显然,公民在互联网发表言论,无疑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范畴,也是监督国家公权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言获罪”现象与法制精神不相容。
为了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8月7日明确:“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
这一规定是从严密诉讼程序的角度,对可能以诽谤罪起诉的案件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防止党政官员滥用公权力。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规定已经在全国实施,对媒体刊发批评性报道也是一种支持。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规定:“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1998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进一步指出:“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2002年7月,著名球星范志毅以《东方体育日报》在2002年6月16日刊登的《中哥战传闻范志毅涉嫌赌球》侵害其名誉权为由,起诉到上海市静安区法院,要求被告向他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万元。9月18日,静安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认定范志毅败诉的判决书中,我国法院首次使用了公众人物概念,阐述了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反向倾斜规则:“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也就是说,在涉及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时,与这些内容相关的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应当被特殊对待,公众人物比一般公民更有义务忍受轻微伤害。
应当认为,这一判决对我国如何正确对待公众人物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既提出了公众人物具有高于一般公民的容忍义务,又恰当地平衡了公共利益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关系。王利明教授在《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一文中说:“被告所做的有关报道不仅满足了公众的兴趣,也是对球队和球员所实施的舆论监督。”“对于有幸参与其中的每一个足球队员,媒体都有舆论监督的权利”。
媒体应当敢于对公众人物实施监督
近年来,我国对社会名流提出批评指责引发的纠纷,大多以名誉侵权提起诉讼。
笔者认为,对涉及公共人物的案件,判决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独立作出,新闻媒体需要解决的是今后还敢不敢刊发监督公众人物稿件的问题。公众人物是大众知情的兴趣重点所在,也是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不少明星人物还时常运用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进行“炒作”,媒体也为明星的“走红”耗费了大量资源。与此相应,公众人物必须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作出一定的牺牲。
就媒体而言,保持对公众人物的舆论监督是因为公众人物事实上与媒体频繁接触,即便是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公众人物的“稍有不适”,也应当对他们的人格权进行适度限制。否则的话,公众人物积极寻求、照单全收媒体给其带来的益处,却容不得来自媒体的些许监督,这对社会公众而言也是一种不公正。
特别是志愿型公众人物是在主观上渴望自己成为公众注视焦点的人,正因为“电视有形象、广播有声音、报刊有报道”,歌星影星的票房价值才能抬高,画家作家的稿酬才能飙升。志愿型公众人物对自己成为公众人物持有的是希望、放任的态度,他们的这种主观意识决定了其应当付出容忍轻微损害的代价。换句话说,志愿型公众人物在利用媒体的力量“走红”之时,就应当同时对自己在媒体面前“丢丑”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也许是出于人性的弱点,谁也不愿意在媒体上“丢丑”,但问题的关键是你有没有做丑事。如果确实做了丑事,公众人物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代价。
引导社会的正确价值取向一定要强化对强者的监督,放大弱者的声音。媒体承担着伸张正义、推动法制、扬善抑恶的社会责任,媒体对公众人物实施监督关系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对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闻媒体对公众人物实施有效监督,既可以遏制强势群体滥用权力,同时能够提醒和促使公众人物时刻保持良好社会形象,也是对公众人物的爱护和帮助。
正因为此,被监督的公众人物不能苛求媒体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反复的核实,只要基本事实无误就应当接受监督。2007年,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讲的一段话特别具有启发意义:“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它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媒体监督)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
按照“实际上的恶意”原则,原告不仅要证明被告贬损人格的内容已经发表,给自己造成了损害,而且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上的恶意”。
这里所说“实际上的恶意”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明知故犯,二是严重失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揭露公众人物违法或者不道德的隐私行为并不是恶意。这是因为,对隐私权的保护并不能推导出“凡私必隐”的结论,如果该隐私违反国家法律或者公序良俗,依然应当根据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允许媒体予以揭露和抨击。为此,媒体应当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坚决地、坚定地对公众人物实施监督。根据“有为才能有位”的原理,我国媒体当前对公众人物的监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过于大胆而是勇气不足。
媒体对公众人物实施监督既要积极更要谨慎
客观地说,有的公众人物一方面十分“珍爱自己的羽毛”,另一方面对自己其他器官的管束不够,一旦自己的丑事被媒体曝光,就动用各方面的资源打官司。
其实,媒体发表的报道是否构成对公众人物的侵权,并不完全取决于被报道者感到名誉受到了伤害,关键是报道的事实是否存在。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内外法院在判断是否构成新闻侵权时所采取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准。事实存在与否具有客观标准,也是可以证实的。当然,应然的可以证实并不等于实然的能够证实,媒体在掌握事实证据方面应当练就更强的本领、下更大的工夫。就监督与反监督的较量而言,媒体对公众人物实施监督,既要积极更要谨慎。积极是无私无畏,更好地体现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谨慎是力求准确,更加有效地实施监督。为此,以下方面特别应当引起媒体重视。
首先,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把报道的事实核实准确。实施对公众人物的监督不是评功摆好,媒体应当对可能产生的风险作出充分的评估。尽管媒体不是检察院,法院也不应当以检察院的起诉标准衡量媒体掌握的证据。但是,被监督者可能采取的对策和节外生枝的能力不可小觑。在监督公众人物时,媒体一定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媒体从业人员千万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基本的证据,尽管报道的内容有些许失准,法院也一定能够作出免责的判决。在审理涉及媒体的侵权案件中,举证的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先由原告就新闻报道的不属实进行举证,再由被告(媒体)就该报道的真实性进行证明;在媒体作出证明之后,原告依然有反驳被告所提供证据的权利,当然被告也有反驳的权利。在这样的举证较量中,原告承担的仅仅是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实质性的举证责任由媒体承担,媒体必须在刊发报道之前围绕证据作出全面扎实的准备。
其次,要围绕公众人物社会角色的相关性进行报道评论。所谓角色相关性,是指新闻报道的内容必须与公众人物在社会中所处的角色相关,不能以猎奇的心理炒作公众人物与其身份不相关的事情。如果新闻报道的内容超出了公众人物的社会角色范围,则可能构成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公众人物的构成比较复杂,实施监督时不能偏离其特定的社会角色。例如,对政府官员等完全型公众人物监督的重点应当是其是否守法守纪、道德是否良好;对明星、知名学者、商界名人等志愿型公众人物,监督重点应当是与其所从事行业有关的行为以及遵守社会公德的情况;对非志愿型公众人物的监督,应当尽可能“就事论事”。例如,某人因为目击某一事件的发生,作为关键情节的,对其的监督应当集中于作证行为。
第三,要准确把握泛指、不点名批评、指名道姓的尺度。无论是报道还是评论都存在尺度把握,尺度把握并不单纯是技巧,决定性的因素是事实状态和所掌握证据的数量质量。一般而言,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只能针对某种不良现象进行概括的、较为模糊的表达,所使用的词汇只能是泛指,而不能具有特指的含义。如果已经掌握了比较扎实的证据,且以不可变更的方式记录下来,在披露或者批评时可以采用不点名的方式。所谓不点名,实际上存在某种程度的暗指,应当“点到为止”。一般地,既然不点名就不要使用逼仄或者影射性的词汇,避免引导对方“对号入座”。不点名的遣词造句,应当为受众提供充分想象的空间,为自己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以能够说明特定的范围、行业为度。凡是指名道姓的批评性报道或者评论,应当既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又客观陈述被批评者的观点。必要时,应当事先持有来自官方的相关文件。
第四,要“平衡报道”,避免媒体成为某一方的代言人。当对公众人物的监督引起诉讼时,媒体应当力求“平衡报道”,客观地陈述双方的观点。所谓“平衡报道”,是指给纠纷双方(特别是诉讼案件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陈述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媒体对任何纠纷都应当保持清醒的中立,充当“观察者”而非“参与者”或者“裁判者”。媒体要有“抢新闻”的意识,但不能搞“媒体审判”,用造舆论的手段干扰法院独立审判。在案件发生的初期,应当允许媒体按照新闻事实作出报道,在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之后,媒体不能继续以新闻事实代替法律事实。因为只有法院的生效裁判才具有终局性,评论一般应当在判决后进行。随着案件审理进程发表的评论,应当符合案件审理不同阶段的特征。只要不是判决已经生效的案件,媒体都应当避免“一边倒”的报道倾向。
(作者为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上海法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扩展阅读
-
- 信阳日报社:基层典型人物最具正能量 2019-04-23 11:38:27
- 北京青年报:将媒体监督纳入"月考"值得点赞 2018-12-05 11:26:23
- 北京青年报:将媒体监督纳入“月考”值得点赞 2018-12-03 11:30:29
- 浙江日报:多管齐下宣传“八八战略”15周年 2018-08-23 12:20:02
- 光明日报:对舆论敲诈决不姑息 2018-08-22 12:15:27
- 北京日报:舆论监督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 2018-08-17 13:22:06
- 新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