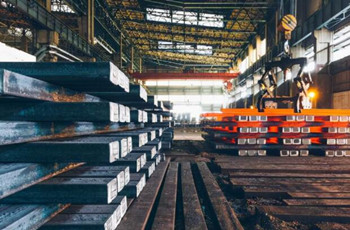对传媒与流言传播关系的再思考(2)
如果说,传媒在“非典”时期的社会角色还有些模糊的话,那么这一次,它的角色非常清晰:它没有犯特别明显的错误,这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言和恐慌的产生与之无关。在抢盐流言泛滥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社会背景--近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发展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尽管公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过分繁重的工作压力、近一段时间来的物价飞涨,各色各样的社会压力以及社会保障措施的不完善都使他们容易感到焦虑。另外,由于包括某些地方政府在内的公共机构都缺乏基本社会诚信,因此即使在平时,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都层出不穷。就在抢盐事件发生的前后,关于瘦肉精的问题还在让公众感到普遍不安,从“三鹿”事件以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公众。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灾难降临,长期积压的焦虑感和不信任感就会像火山喷发一般喷涌而出。也就是说,上述一系列的因素共同建构出了抢购食盐的恐慌和流言。所以说,这次核辐射危机之后的流言泛滥是一个很好的晴雨表,它提醒我们,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中国社会仍然不够成熟不够平衡,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责怪传媒就能解决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次的流言传播与传媒的表现几乎没有关系。
最终平息问题的也不是大众传媒,而仍是公众自己。这一次,自媒体似乎成为了一个辟谣的重要阵地。确实,第一条流言是来自互联网:“3月15日晚,一篇题为《以碘“抗”核?或许有用,但没必要》的文章在果壳网发表--那两天,‘服用碘片可抗核辐射’的说法在国内网络上风传。”然而这一次自媒体的自净能力令人惊叹:比如新浪微博在3月16、17日两天内,出现的有关“抢盐”的微博多达245万条。在微博中,许多网友用段子、对联和谐音成语的方式反讽了“抢盐”的行动。另外,各种反讽的短信在手机上广为流传,与“非典”时期的情形也多有不同--那时几乎所有的手机短信都是流言。自媒体强大的渗透力最终导致了抢盐者在社会生活中也遭到了同样的鄙视和嘲笑。自媒体的自我净化能力体现出了民众自身的反思能力,这一点与8年前的“非典”情形大为不同,让人想起弥尔顿的那个著名的判断:真理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在一篇极其重要,但又常常被人忽视的论文《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社会行为》中,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了大众传媒产生强大影响力的三个条件:其一是在垄断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传媒的价值观、政策或公共形象的扩散;其二是渠道只有为既存态度和价值观提供传播路径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其三是媒介只有与面对面交流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才能取得最佳效果。由于这三个条件在现实社会中同时被满足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媒介往往无法充分展现其社会权力。也就是说,早在半个世纪前,两位传播研究领域重要开拓者就已经为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定下了基调。首先,大众传媒是可能取得强大影响的,但前提是它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它要维护现有价值还要辅之以人际传播和社会动员。这三种情形在当代社会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因为信息的垄断和反宣传的缺失已经很难实现,大众传媒与人际传播相结合的难度也很大,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因此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在突发性事件上,由于它在传递与现实舆论不太一致的信息时,往往没有太大的效果。因此,指望大众传媒劝说公众不要相信他们已经确认的流言,不会有太大的作用,这当然是由于传媒作为诱因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所以,流言不是在传媒的作用下消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解决的:流言和谣言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现实的检验,因此,当民众发现自己的错误后,他们会做出相应的修正,就像这次“抢盐事件”中他们在新媒体上所做的反思一样,而这时大众传媒的催化剂式的辟谣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所以,现在基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流言的传播与传媒是否失语并无必然关联,尤其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我曾经在回溯“非典”时期的流言传播研究时指出:“尽管传媒确实要担负一定的责任,不过当时很少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传媒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这种对媒体的大肆批判与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开脱了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笔者认为,将责任推给传媒恰恰说明了传播学研究的狭窄视野,缺乏不断追问的能力和精神。”然而现在看来,这样的批判还没有说到问题的点子上,其实当时的研究者还是基于一种“魔弹论”的立场在分析“非典”时的媒体。在他们看来,只要大众传媒做得对,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只要大众传媒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后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魔弹论”这种在专业意识中已经被唾弃了很多年的思想是如何潜伏在传播学者的集体无意识中的。
从事传媒研究的学者的通病就在于将传媒看作是社会运作的中心,而无视传媒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正确定位。传媒的本质是一个窗口,是一种深层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自我表达的平台,因此,它是一种景观,一种表象传播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如何透过这一景观和表象,去分析人和社会,而不是以这一景观和表象为中心,重新安排构成社会结构的其他元素。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分析人和社会在传媒或交流中的呈现,分析传媒景观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比我们去研究传媒与人和社会的因果关系要有意思得多,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作为一个传播学者,我很能理解我的同行们为什么会下意识地以“魔弹论”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如果传播业对社会的影响真的是那么有限,那么还需要传播研究者的专业研究吗,还有必要投资做传播研究吗?”他们想证明传播学的有用性和对人与社会的重大解释力。然而,我们不能用“传媒中心论”或者是“魔弹论”来回应对传播学有没有价值的质疑,这些理论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它们是一种武断和缺乏依据的理论,而更在于它们是一种过于膨胀的专业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去证明传播学的价值,其结果一定会南辕北辙。就像“非典”的研究,其实它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结论,而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结论,它想又快又好地给出答案,却不仅肤浅而且错误,它把传播学变成了一种新闻评论或社会评论。传播学如果不能超越这种专业意识形态,它就会像现在一样,在人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上一直没有话语权。
扩展阅读
-
- 新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