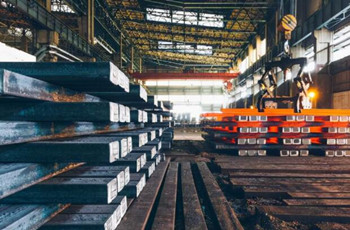郁达夫编辑思想探究
与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相比,许多人对于他的新闻副刊编辑事业知之甚少。透过历史的纱幕,拨开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华民族的苦难之门,文学家郁达夫在远离故土的新加坡,将生命陨落前最后的光华献给了祖国抗日救国的新闻事业。
郁达夫主持《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历史背景
1938年,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年代,日军不仅在军事上占据极大优势,快速占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并且在新闻舆论上采用“以华制华”的战略,实施新闻封锁和高压控制,实行“新闻新体制”,以图控制在华新闻舆论,为其侵略行径编造辩护词。郁达夫曾于1938年1月亲临台儿庄前线劳军,目睹抗日军民在物资极其匮乏的艰苦条件下拼死抵抗的事实。
当年散居在南洋各地的华侨约400余万人,都具有中国国籍(当时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其中不乏像陈嘉庚那样爱国的富商大贾,华侨中蕴藏着巨大的爱国热情。据相关资料记载,东南亚华侨在中国抗战中所捐献的钱款物资,在总数上仅次于美国,而1941年前则占外援的第一位。
郁达夫正基于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持抗日战争、掌握南洋新闻舆论阵地主动权的考虑,在《星洲日报》创办人胡文虎的盛邀下,于1939年1月至1942年2月,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繁星》编辑,还曾一度担任《星洲日报》主笔。郁达夫遵循抗战宗旨,将当时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办成了在南洋文化界一份最出色的“抗战副刊”。此间,他先后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时同时编过八种,如《星洲日报半岛月刊》的《星洲文艺》专栏,《星光画报》文艺专栏,《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教育》周刊,以及主编《华侨周报》等。当时国内抗战处于白炽化状态,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政治经济因素复杂。为宣传救亡和抗战,郁达夫在这三年间从事新闻副刊编务工作十分努力,每天伏案工作平均十小时以上,笔耕平均在四千字以上。每天上夜班审读最后新闻电稿后才下笔写社论,等看完清样付印往往到凌晨,而白天还照常参加各抗日组织的社会活动。这一时期,郁达夫共在各报刊发表了包括社论、政论、随笔、文艺评论及书信等在内的文章共462篇,其中政论时评就有104篇。
郁达夫曾说,他此次南来的目的是“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正因如此,郁达夫在极度繁重的工作重压之下依然保持充沛的精力,编报纸,撰社论,写政论杂文,以饱满的激情关注国内国际时局的变化,给抗战军民以方向以鼓舞,同时培养华侨文艺青年,推动更多的人士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
郁达夫的副刊编辑思想解析
副刊的界定及其定位问题,学术界颇具争议,但是无论是“报屁股”还是“报尾”,都是正刊所不可或缺的补充。抗战时期的副刊比之于和平时期,显然有很大的不同。抗战期间的副刊在面临亡国的危机之下,除了具有强烈的新闻性、时代性之外,更兼具鼓动性、呐喊性和激励精神。当年为抗战救亡,著名的文学家参与副刊编辑较多,如萧乾在《大公报》担任《文艺》副刊编辑,夏衍在《华商报》副刊《灯塔》任编辑等。郁达夫在编辑《星洲日报》副刊的三年多时间里,其编辑实践一如其人,感情真挚见情见性;副刊写作也一如其文,坦荡磊落正气率真。
郁达夫在三年多的副刊编辑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副刊编辑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1.强调编辑的良知与战斗精神,强化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
抗战救亡是《星洲日报》的宗旨,其正刊的新闻报道具有客观事实性,而副刊在郁达夫的主导下,则对新闻事件进行主观解读,使之具有诠释、引导、强化的作用,将爱国主义与抗战必胜的信念灌输给南洋的民众。纵观郁达夫一生,爱国主义是其精神的支柱,而且越到晚期越显执著。面对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和汪伪汉奸们的蠢蠢欲动,郁达夫在代理《星洲日报》主笔及主编副刊《晨星》、《繁星》期间,集中发表了更多充满浩然正气、宣传抗日战争必胜的鼓动性的作品,如《“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会》、《“八一三”沪淞抗战的意义》、《“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抗战两年来的军事》、《粤桂的胜利》、《谈轰炸》等几十篇。必胜的信念使他明确了战争的性质,使更多的同胞看清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也更加明确了战争必然向我方胜利的方向发展。他说:“我国士兵个个都以驱逐敌寇出境为天职,敌忾心的一致高涨,与夫保国家保民族的信念的例外坚强,是比抗战当初更增强了十倍。”在《估敌》中称:“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这些文章充满了时代的号角之声,充满了赤子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反映了郁达夫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抗敌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作为一名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崇高、正直的人格魅力。
2.认真负责的编辑态度,热心培养青年作者的奉献精神。
郁达夫曾在《编辑者言》一文中表明自己的编辑态度:“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投稿者的天才与抱负更不得不尊重”。他不轻易改动来稿的文字,一旦改动总能使作者心悦诚服。《星岛日报》外勤记者石蕴贞回忆郁达夫说:“他编副刊《晨星》,对青年投稿者特别爱护,许多青年朋友投去的稿件,能用的他都用上;要修改的,他认真做了修改。他不轻易改动稿中的文句,但被他改动了的,每一句或每一个字,都使作者心悦诚服。有个朋友甚至说他是点石成金。对不能发表的稿件,他也经常请作者来谈,说出自己对作品的意见,这是许多编辑做不到的。”一名大作家,能如此认真负责地审阅处理众多稿件,着实不多见。郁达夫的认真负责精神,感动和鼓励一大批南洋的文学青年。
在新加坡的三年中,郁达夫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十分重视培育青年作者,扩大副刊的作者队伍。郁达夫平易近人、热情指导的态度令青年作者难以忘怀。在他身边工作过的青年作者就达二十余人,受过他指点的不计其数。经他从来稿中发现并不断联系指导而后很多成为了著名作家,成为了以后新加坡文学的中流砥柱。对于新人创作的优秀作品,郁达夫毫不吝惜版面、笔墨,亲自撰写评介文章或作序予以推荐。郁达夫把副刊园地当作他培育文艺新人,传播中华文化的苗圃,而他则是辛勤的园丁。王余杞在《“送我情如岭上云”——缅怀郁达夫先生》一文中,曾用“平生风谊兼师友”形容郁达夫。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回忆诗人郁达夫》中说:“他看稿认真,提携过的文学青年,如刘前度、苗秀、王君实、冯蕉衣等后来都成了名作家。”
3.重视介绍国内文学艺术作品,辛勤灌溉南洋文化绿洲。
1938年郁达夫到达新加坡,想为抗战在海外建立一座文化中继站。当时的新加坡受战事影响,可以说是文化的沙漠。马来亚华文文学,虽然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新文学,但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内陆,“一般风气未开,知识灌输还不能普遍”,郁达夫在从事编辑的同时,实际也起到了“拓荒者”的角色。郁达夫主持副刊,用他的话说就是“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做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为此他邀请中国许多学界、文艺界名人在《星洲日报》投稿,或来新加坡演出、讲学。三年间,文学界如郭沫若、茅盾、夏衍、成仿吾、冰心、柯灵等都在《星洲日报》发表作品,文艺界先后有昆明漫画展览团、武汉合唱团,画家徐悲鸿、刘海粟,篆刻家张思仁,歌舞家紫罗兰,演员王莹等到新加坡演出展览,郁达夫热情接待,大力撰文宣传。
在介绍国内文化的同时,郁达夫着力培养独特的南洋文艺。他在《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南洋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南洋文艺的地方性和独特性,应该怎样使它发扬光大,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扶植发展南洋本土文化,这也是郁达夫大力培养当地文学青年的主因之一。
扩展阅读
-
- 新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