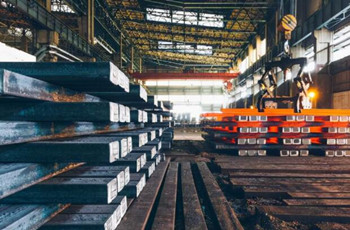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采访札记]一次红色寻访,一场心灵之旅
“追寻1921南湖‘七一’记忆”的报道见报后,总有好奇的同事、读者向我打听,寻访“一大”代表李汉俊、刘仁静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趣闻逸事?说真的,短短一个多星期,我和同事从嘉兴南湖出发,辗转湖北孝感、应城、潜江、武汉以及上海一大纪念馆等地,一路奔波下来,趣闻逸事虽谈不上,但的确有让我无法释怀的人,难以忘却的事。或许他们只是在红色寻访中一闪而过,却让我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旅。
路上的人
他叫匡文杰,孝感日报视觉中心主任。与他的会面,是我们寻访的起点。2011年4月12日下午,当我们的航班到达武汉天河机场,他已经和同事在出口处等候多时。超过一米八的高大身材、利落的板寸发型,浓重的孝感口音,手捧一只半旧保温杯……一眼瞥过去,这个如岩石般憨实的男人,曾让我们误以为是当地媒体安排接送的司机。
从武汉到孝感,从孝感到应城,整整一天半的采访,他开着一辆八成新的小轿车,载着我们跑遍“一大”代表刘仁静故乡的角角落落。我们做访谈时,他在一旁安静地翻报纸;大家一起热闹地讨论报道思路时,他旁若无人地摆弄摄影记者的“长枪短炮”。
或许这次以踪迹寻访、历史临摹为主的采访活动,没有太多影像参与空间,但这位看似心不在焉的“司机”却一路随行、毫无怨言。直到快分手时,我们才知道,那辆随时待命的采访车是他的私车。如果不是寻访故乡走出去的“一大”代表,谁愿意为一群素昧平生的外地记者当司机?
他叫罗仲全,潜江博物馆老馆长,潜江人亲切地称之为“罗老”。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寻访名单中,原本没有他的名字。安排对他的采访,全拜潜江市委报道组的大力推荐——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故乡,罗老是当之无愧的“两李专家”(“两李”指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
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罗老的讲述略显琐碎。但他口中支离的细节却成了我们潜入历史暗河的宝贵线索。几十年来,英年早逝的李汉俊是潜江人记忆中的空白,为了重拾这段被遗忘的红色历史,他无怨无悔地求索了58年。在全国热衷于李汉俊研究的专家、学者中,论名气和理论水平,罗仲全算不上数一数二,但这种执着却无人能及。
这段意外采访经历,被当做新闻现场,写进了李汉俊的寻访报道中。罗老也在见报后不久,拨通了我的手机。远在千里之外的他热切恳求,哪怕自己出钱,也要买上几十份当天的《嘉兴日报》。因为他要让更多潜江人了解李汉俊,早日在故乡建起李汉俊纪念馆。如果不是出于对先烈的由衷敬佩,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从何而来?
她叫李声(香奇)(读音yi二声),是李汉俊唯一在世的子女,为了找到她,我们不惜大海捞针。然而,这场事前被我想像的轰轰烈烈的采访,意外地平淡如水。虽然热情地为我们准备好了大量照片和文字材料,但李声(香奇)坚持历史地看待父亲:对建党贡献重大,从未放弃过信仰,但也有缺点,比如投身革命时间短,有过脱党经历。
这位一家四代都是武汉大学教授的睿智老人,不喜欢高谈阔论、玑珠妙语,她对父亲的描述,充满了生活的温情和细节。在她的记忆中,从未谋面的父亲一直活在她和母亲心里,在漫长的艰苦岁月中,给了她们生活下去的勇气。“父亲教会母亲和我自立自强”,这句话她在采访中重复多次,让我们跨越时空,看到了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位学识丰富的师者、一名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先驱。如果不是对父亲信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我们又怎能从一位耄耋老人身上看到如此的淡定与从容?
路上的事
这次红色寻访,最关键的转折来自一篇几乎被遗忘的小文章。做采访功课时,我专门找到已先行踩过点的晚报记者。没想到他说,李汉俊的故里只有一座碑,刘仁静什么都没留下。我禁不住低头蹙眉,心一下子就凉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访什么?
浩如烟海的网文和理论文章,大多与南湖革命纪念馆李允副馆长介绍的情况差不多,只有一篇不足千字的小论文里提到,李汉俊的小女儿是武汉大学化学院退休教授。我一看日期,已经发表了好几年,屈指一算,李教授如果在世,也要83岁高龄了。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联系上了母校武汉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门。按照我们提供的线索,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李声(香奇)教授,并专门派武汉大学电视台将我们采访的全程录像、存档。事后,武汉大学新闻中心张全友副主任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嘉兴日报这次寻访,武汉大学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一位“一大”代表的子女了。顺着李教授这条线索,我们又在武汉大学档案馆沧海拾遗,收获了不少“宝贝”。比如作为武汉大学最初的组办者之一,李汉俊是中国最早在高等学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的人,因为课讲得好,慕名而来的人经常把教室窗台外的位置都站满了,一名学生直到80多岁还保存着当年的讲义。
这次红色寻访,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发现了一座有记忆的城市——湖北应城。李汉俊的故里还有一座纪念碑,刘仁静的故里可真是什么都没留下。昔日的泥泞小道,如今已是水泥路,刘家老宅也早就成了繁华的商业街。这种窘境,连热情接待我们的当地媒体也很无奈:“这样的报道我们也没做过,这次跟你们一起学习!”
幸运的是,这位“少小离家”的“一大”代表始终是故乡人引以为荣的骄傲,拥有为数不少的“粉丝”。从应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董建军那里,我们了解到,几十年来,以党史研究员、地方文化爱好者为主,应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刘仁静研究群”。这些或专业或业余的研究者前赴后继,接二连三生产出《最后的同志刘仁静》、《刘仁静传》、《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等专著或理论文章。更为可贵的是,这种红色记忆还在一代代延续下去,68岁的吴树森老人曾是应城“刘仁静专家”,这几年,他40岁的儿子吴学超也成了颇有建树的“刘粉”。通过他们的讲述,刘仁静在我们眼里从平面走向立体。
这次红色寻访,最难忘的是武汉闹市区曲折的寻碑之旅。“有位‘一大’代表李汉俊,您知道吗?”“谁?”“李汉俊。”“李汉俊?没听说过。”“湖北人啊,有这个人吗?”“不晓得。”“不知道。”这是我们采访小组在武汉街头与出租车司机、市民的典型对话。
2011年4月19日下午,我们来到寻访的最后一站——武昌区卓刀泉,打算在李汉俊烈士墓碑前取景。没想到,经过无数次拒载,直到下午6点,还未成行。最后,一辆“黑车”司机终于答应 “找找看”。上车后,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要不是看你已经被五辆车拒了,我也不带你,这地方太‘冷门’了。”经过三易路线,我们终于在武昌卓刀泉庙背后,找到了埋藏着李汉俊遗骨的小山头。
走进山上那片曲曲折折的小树林,不知道拐了多少弯,寻觅已久的李汉俊先生墓碑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夕阳余辉下,一个人站在郁郁葱葱的半山腰,激动恍惚间,我突然感觉这次寻碑之旅宛如此次对李先生的寻访,线索零零碎碎,记忆支离斑驳,行程几经曲折,终于,在接近终点时柳暗花明。
寻访结束后,我把稿子交给南湖革命纪念馆李允副馆长,当我忐忑地向他征询意见,他却反问我:“李汉俊的墓碑真的在武汉卓刀泉闹市区的犄角旮旯里吗?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找到,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到现场看看。”
让我无法释怀的人是一位普通的媒体同行、一位执着的地方考古专家、一位坚守父辈信仰的一大代表后人;令我难以忘却的事是一篇躺在故纸堆里的小文章、一座不因繁华而失忆的城市、一次曲折的寻碑之旅。
或许三个平凡的人、三件普通的事,不足以支撑起一次红色寻访的全程,但至少能为我们搭起一座跨时空的桥梁。从南湖的一只小船到一个大党的成长, “其始也简,其毕也钜”,我们党开启的艰难而辉煌的历史航程不也是由一个个小细节缀连而成的吗?
能亲身参与这次以80后记者为主体的采访活动,我是幸运的。遥想当年,13位代表在红船上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时,他们也大多青春逼人。当我和同事们从南湖出发,去接近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开启的是不仅是一段红色寻访,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旅。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人和事,恰恰是宏大历史在现时代的投影,让我们与一大代表隔着九十年岁月展开了青春的对话。
在路上,我们追寻遗迹、临摹历史、深思人生;归来后,我们将所知所闻、所感所想,通过“一件文物、一次寻访、一个现场、一场对话、一段寄语、一种启示、一组微博”等“七个一”的形式与读者分享,和他们一起打开1921年南湖“七一”记忆之门,一起融入红船记忆与精神传递。
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轻党报记者为建党90周年献上的最好礼赞。
注:本文作者系嘉兴日报社记者,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岁生日,嘉兴日报以“从南湖出发,我们共同记忆”为主题,推出“追寻1921年南湖七一记忆”大型系列报道,从3月15日开始先后派出6个采访组13路记者赴党的“一大”代表故里寻访。今年4月中旬,本文作者在湖北、上海等地对刘仁静,李汉俊二位“一大”代表进行了寻访,并先后于2011年5月16日、23日在嘉兴日报分别刊发了《李汉俊:南湖火种在珞珈山下熊熊燃烧》、《刘仁静:“小马克思”的红色青春》两篇寻访稿件。
扩展阅读
-
- 新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