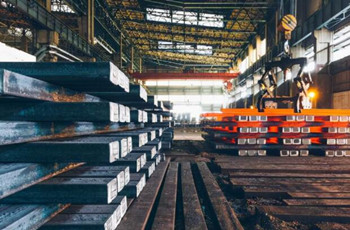传媒投资热的隐患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景象:在当今中国,从各级政府,到资本市场,再到新兴的互联网领域,人人都在谈论传媒产业的“投资价值”。
最早把目光投注到这里的是风险投资家们。早在三年前,已经有很多天使投资者、VC或PE就开始在传媒产业链上进行布局了;而IPAD、微博等新产品、新技术的诞生与病毒式的增长,更让传统的媒体生态发生了让人眩目的变局;在10月份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最重要的主题,更是把这一态势推拱到一个前所未见的热度。
当政府、资本与技术都达成共识之后,还有什么可以阻滞文化传媒产业的兴盛?
然而,我们接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传媒业天生有社会公器的属性,它与资本的逐利属性将构成矛盾。在未来,有哪一种力量和制度可以对之进行均衡?同时,人文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性与科技人员的工具理性,又如何互相钳制和妥协?
在中国的传媒史上,这是一些没有发生过的疑问。自晚清政府开放言路之后,到1949年之前,没有一位投身于传媒的人士是以逐利为最高目标的,民国最成功的出版人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曾有人问他,“你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个文人?”他满脸彤红,视此问为羞辱。
进入1949年之后的相当时期,传媒业不对私人开放,因此也不存在这类问题----政府将传媒当成“私器”或“喉舌”,那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而正是在最近十余年的互联网革命中,传媒市场的国有垄断格局逐渐被新技术所打破,当今中国的新闻门户、视频门户、在线图书销售门户等等,均由民间资本所控制,而从现在开始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更是加速了传统传媒业的没落以及整个产业的市场化转型,在这其中,资本和新技术似乎成了主导性的力量。总体而言,这当然是进步的景象,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个重大的人文隐患。
在西方的社会进步史上,曾经有两个时期,思想界认真地讨论着这个话题。第一次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思想启蒙年代,培根所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推动了科学思想的解放,然而同时,“人文科学最终不是沦为自然科学的糟糕复制品,就是披上了新信仰的外衣”。第二次是1940年代二战末期的原子弹爆炸,它所造成的破坏力以及不可控制性,让人们又一次认真地思考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进步中应予扮演的角色。
德国当代思想家沃尔夫.勒佩尼斯把推动社会进步的精英阶层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具有坚定信念的人”,另一类是“多愁善感的人”,前一类人以毋庸置疑的姿态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而后一类人则“迫使人类控制自己的感情”,有意思的是,政府官员、资本家、科技人员都属于前者,而人文知识分子则属于后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在当今的欧美国家,“多愁善感的人”惟一可以与前一类人构成社会均势的“领地”是文化传媒业,因此在近年来,我们便不出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景象;当有互联网背景的资本向传统媒体发动购并行动的时候,往往会遭到最激烈的抵制,即便在资本层面失去了控制权,但仍能保持内容制造和思想传播上的独立。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景象会同样发生吗?
人文科学从本质上来讲是伦理学,而传媒因其特殊的公器属性,伦理的特征尤为显著,道德理性、敬畏和节制是一个健康的传媒生态环境的必备条件。
在新的传媒生态快速衍变和形成的过程中,如果以逐利为目标的风险投资资本以及以科技进步为"终极目标"的技术力量成为了结构性的主导势力,那么,将可能出现两个景象:
首先,为了提高盈利能力,对低俗文化的迎合将成为传播产业的主流,然后,出于“对投资人负责”的职业天性,传媒拥有者将屈服于权力的挤压,并向之寻租。而最终,权力、资本与技术将达成新的“利益契约”。
而可悲的是,长期受到压制和部分地丧失了独立能力的人文知识分子集团似乎根本无法阻拦这一态势的发生。对权力的抵抗、对资本的警惕、对技术革命的均势,都好象不可能发生。
从今往后,在追求“快公司”效应和投机暴利能力的中国市场上,不知道将会演出怎样的悲喜剧。
在传媒产业炙手可热的今天,我的这些“多愁善感”显得那么的迂腐、矫情和不合时宜,但是,它也许真的存在?
扩展阅读
-
- 新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