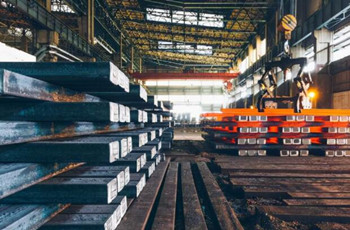浅析社会极端事件报道“以死抗争”框架的滥用
展锋人物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新闻学教研室副主任刘大勇。
近一个时期以来,自杀、凶杀等社会极端事件成为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以死抗争”的新闻框架在此类事件报道中被屡屡使用。事实证明,“以死抗争”框架在唤起受众注意、制造情感共鸣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但也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极端事件都适用于“以死抗争”框架,不加选择和节制地使用这一框架,将使其传播效果事与愿违。
“以死抗争”框架的使用形式
学界通常认为,新闻框架是记者在处理信息和意义时必然有的整体性的思考基模,或中心意义的组构方式。我国新闻媒体在社会极端事件报道中使用“以死抗争”的框架通常表现为:围绕冲突中“弱势”一方为维权而以命相搏选取新闻事实,突出强调以“弱”抗“强”行为的悲惨性和正当性,并结合社会矛盾赋予抗争个案以广泛的社会意义。针对社会极端事件与当事人抗争行为关系的直接与否,这一新闻框架在使用中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原生型运用。“以死抗争”新闻框架的原生型运用,是指社会极端事件在当事人维权的过程中发生,作为一种典型的身体抗争形式,新闻报道围绕侵权与维权的矛盾事实进行报道,通过强调弱势一方为维权而死伤的事实凸显“以死抗争”的新闻框架。例如在江西“宜黄事件”的报道中,钟家三口在自家屋顶上自焚的景象成为了社会舆论的引爆点,新闻媒体大都将钟家自焚解读为以死抗拒暴力拆迁。为进一步凸显钟家三口以死抗争的深层原因,新闻媒体还对悲剧的始作俑者——抚州市宜黄县的有关领导的强硬态度进行了聚焦,强化钟家自焚惨剧反映出的制度不公问题,并引导受众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新闻媒体对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不满钓鱼执法而自断手指等社会极端事件的报道,均属此类。
嫁接型运用。“以死抗争”新闻框架的嫁接型运用,是指社会极端事件与维权存在间接关系时,新闻报道通过嫁接当事人被侵权的新闻背景的方法,指认极端行为的抗争性质。例如2008年“杨佳袭警案”,最初以单纯的犯罪新闻进入公众视野,但随着新闻媒体放大了杨佳袭警前投诉上海警方未果的新闻背景后,这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成为了带有一定合理性的“抗争”行为。再如,2010年5月福建永春91岁老人刘线“闻拆自尽”,期间并未发生过任何主张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举动,新闻媒体在报道其亲属认为老人自尽与强拆有关的态度的同时,向受众提供了大量关于当地老人难以租到房屋居住的新闻背景,使拆迁方强求老人拆迁的要求成为了潜在的侵权事实,从而为受众构建了高寿老人为抗拒强拆而自尽的基本认知。
联想型运用。“以死抗争”新闻框架的联想型运用,是指社会极端事件与当事人的维权行动缺乏确切联系时,新闻报道通过有目的地向受众告知有关情况,诱使受众将社会极端事件联想为“抗争”行为,进而将报道纳入到“以死抗争”的新闻框架。例如“富士康连环跳”事件报道,聚焦这一事件的各大媒体自始至终没有说明员工自杀的确切原因,以及跳楼员工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相关报道,而是在关注连续自杀的同时不断指认厂方是“血汗工厂”,从而引导受众在侵权与自杀之间进行因果关系的联想——将连续自杀行为理解为对“血汗工厂”的抗争。
暗示型运用。“以死抗争”新闻框架的暗示型运用,是指新闻事件尚未发展到当事人伤亡的地步,新闻媒体通过放大某些新闻细节,暗示事态即将恶化为“以死抗争”的社会极端事件。例如,2010年6月的“土炮维权”事件,其最初的报道是典型的“游戏框架”——新闻媒体以杨友德使用“土炮”抗拒强拆的成功与否为中心进行报道,凸显双方在攻防过程中的策略和行动,刻意突出事件的戏剧性和观赏性。但在随后的报道中,就开始不断放大维权人士杨友德谈论拼命、留下遗书的细节,并添加强拆者显露杀机等内容,预示当事人的“抗争”将会出现惨烈伤亡。如《新京报》刊登的《村民自制土炮轰拆迁队续:留遗书让儿子继续维权》中这样报道:“在后果出现之前,他说‘我只能拼了’。”“杨友德:我的遗书是写给我儿子的。我告诉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体。还要依法维权,拿回我们应得的钱。”而事实上,“土炮维权”最终以杨友德与拆迁方达成协议而告终。
总的来看,“以死抗争”新闻框架的四种运用手法中,除原生型运用较为客观外,其余三种均较为明显地体现了新闻媒体的主观判断色彩,这为滥用“以死抗争”框架创造了条件。
“以死抗争”框架的滥用现象
必须看到,“抗争”并非是所有社会极端事件的主要属性,具有“抗争”属性的社会极端事件也并非都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新闻媒体在报道社会极端事件中,不加选择地使用具有弘扬抗争意味的“以死抗争”框架,形成了这一框架的滥用现象。
在漠视个体生命的基础上弘扬“抗争”。“死”(或以命相搏)是“以死抗争”框架的主要新闻点,过分使用这一框架报道自杀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极端事件时,客观上造成对生命的漠视。在“富士康连环跳”报道中,为体现“抗争”的惨烈性,大部分新闻媒体都将连续自杀作为聚焦的“新闻点”,“×连跳”等突出连续死亡的标题屡见报端,有媒体还以“新闻回顾”的方式列举了富士康的历次跳楼自杀事件,却始终没有任何报道揭示富士康员工自杀的确切原因,以及自杀者的详细故事。尊重和敬畏生命无疑是新闻工作所有底线中最不可逾越的一个,炒作死亡即是对生命的漠视。
在盲目同情弱者的前提下报道“抗争”。“以弱抗强”是“以死抗争”框架运用过程中价值判断的重要来源,同情支持弱者是这一框架价值判断的主要指向,而将强弱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造成了受众对弱势方的盲目同情和认可。在邓玉娇案的报道中,有的媒体在案情调查尚未清楚之前,即将“弱女杀恶官”作为自己的报道倾向,这使得邓玉娇在案情大白之前即被舆论指认为“烈女”甚至是“侠女”。
在淡化法制意识的意味中解读“抗争”。在涉及严重刑事犯罪的社会极端事件报道中使用“以死抗争”框架,往往会引发淡化法制的不良社会效应。例如“杨佳袭警案”本来是一起典型的恶性犯罪事件,一些新闻媒体却用“以死抗争”框架放大事件中的抗争情节——杨佳投诉闸北区公安分局警员未果,用抗争属性取代事件的犯罪属性,竟然使得血腥暴行获得了一定的合理性。维护法律的尊严应该是新闻媒体报道违法事件的首要前提,纵然事件中有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以死抗争”的新闻框架依然不是新闻媒体唯一的选择。遗憾的是,之后的“永州枪杀法官案”等恶性犯罪事件的报道,都有媒体不当使用“以死抗争”新闻框架的现象。
在迎合极端情绪的思维中炒作“抗争”。社会极端事件除了反映出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弊端,也体现出我国转型期社会中较为广泛存在的极端情绪——漠视事实真相,完全按照身份、地位和利益进行划分、站队,但凡涉及权力部门、弱势群体的矛盾冲突,就立即定性为倚强凌弱的社会不公。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新闻媒体不是积极疏导极端情绪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进行迎合,在有失公允的前提下运用“以死抗争”框架报道社会极端事件。在“邓玉娇案”引起社会关注的早期,某知名报纸曾在《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致命邂逅》的报道中客观报道了死者邓贵大家庭的意见和情况,此文旋即遭到网络舆论的口诛笔伐,此报在随后的报道中只好回归“民意”而淡出公众视野。
滥用“以死抗争”框架的负面效应
滥用“以死抗争”框架报道社会极端事件势必产生如下的负面传播效果。
不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理性认知结构。“以死抗争”新闻框架的嫁接型运用和联想型运用,在构建社会极端事件和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上是值得商榷的。以系列“杀童案”中的“南平血案”为例,辞职之后生活无着落、恋爱失败、受周围人员闲言刺激,是凶手郑民生供认的三条作案原因。郑民生因此迁怒社会,可见其个人心理因素是行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一些新闻媒体却运用“以死抗争”框架放大郑民生一直强调的“是社会冷漠造成悲剧”的新闻细节。这在客观上给受众树立了非理性的认知结构——将所有社会极端行为都归咎于社会和体制。这样的认知结构对解决相关社会矛盾是缺乏建设性的,“南平血案”报道后接连发生的几起杀童案,除了与报道的示范效应有关外,“以死抗争”的新闻框架是难辞其咎的。
不利于营造化解矛盾的社会舆论氛围。在社会极端事件的报道中滥用“以死抗争”框架,客观上引导受众忽略了其他抗争手段的有效性,构建了生命和公正的二元对立关系,强调了社会矛盾的不可化解性,为社会灌输了消极情绪,其结果是助长社会极端心理,导致看客心理和社会戾气的泛滥和膨胀。复旦大学学者滕五晓认为,当前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状,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如果再加上某些不公正待遇,他们的长期压抑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小事或者突发事件,而最终因“个人仇恨”去“报复社会”。在此形势下炒作“冲突”和“拼命”,其后果无异于火上浇油。
不利于构建平等对话的社会公共领域。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媒体的不断发展,新闻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地位和价值不断凸显。而这一地位和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利益各方是否能够平等地交流,这种交流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的思考。旨在煽动公共情绪的运用“以死抗争”框架报道社会极端事件,将使新闻传媒从公共领域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某一种宣泄工具、攻击武器,促发“舆论暴力”。“舆论暴力”的本质是对话语权的独占,它破坏了新闻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和协商性,使新闻传媒沦为矛盾某一方的工具甚至是武器,尽管可能最终达到了伸张正义的目标,但手段的不正当性和野蛮性却为犯下更大的错误埋下了祸根。
不利于建立依法维权的社会基本认知。作为“以身抗争”形式之一的“以死抗争”常是“以法抗争”无效之后的无奈选择,社会极端事件也常由此而生。在淡化法制的意味中使用“以死抗争”框架报道此类社会极端事件,在客观上给受众构建这样的基本认识:权利被侵害→以命相搏→媒体介入→舆论哗然→上层关注→问题解决。显然,抗争行为的极端化体现的恰恰是我国法律和制度方面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应该从法律和制度渠道来寻求,在法律和制度之外强调舆论的裁判力恰恰与民主和法治精神相左。新闻媒体由社会环境的监察者、思考者,转变为独立于法律和制度之外包打天下的“‘报’青天”,其体现的并不是现代民主和法制精神。这样的新闻报道只能使权利受侵害者更多地涌向新闻媒体,使法律和制度的公信力更加弱化,使更多的社会冲突恶化为社会极端事件。
媒体如何报道转型期的社会极端事件
新闻媒体该如何报道社会极端事件,如何引导社会认知并培养具有建设性的认知习惯,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担当社会责任而非空谈社会问题。德国社会学家乌尔西里·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随着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社会要素不断增多、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风险和危机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造成的后果也更加严重。今天,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极端事件增多正是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严峻社会风险的突出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新闻传媒就更需要担当起风险治理和预警的社会责任,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构建和谐统一的社会观念、进一步推进制度完善,在社会极端事件的报道中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进行舆论引导。
构建社会和谐而非强调社会分歧。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割不断加剧。经历过利益绝对平均化的传统社会熏陶的民众,正在经历着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剧烈冲击。近年来备受社会瞩目的社会极端事件中,均可看出由此带来的心态失衡和文化迷失。正如著名新闻学者李彬所说:“中国当代的问题纷繁复杂,难以厘清,但最大的危机恐怕在于人心的涣散、社会的碎片化。”新闻舆论的社会批判作用和社会构建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在社会极端事件中片面强调社会构建作用无异于扬汤止沸,而片面强调社会批判作用则等同于火上浇油。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现状来看,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心理动荡和社会调整,恰恰需要构建和谐统一的社会观念以及更加科学的制度安排,发展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旋律。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构建作用应该是新闻舆论发挥社会功能的最终落脚点。
着眼解决矛盾而非单纯展现矛盾。新闻媒体面对带有抗争性质的社会极端事件,应将重点聚焦于当事人缘何不得不采用杀人杀己的暴力反应性方式实施抗争,国家和社会应该共同对他们施以什么样的援手、进行怎样的改变,从而在公理和法制的框架内防止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而非对抗争行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探究,甚至煽动本来就已经焦躁不堪的社会情绪。为被侵害权利的社会个体讨回公道固然是新闻媒体面对社会极端事件的重要价值之一,但解决个案中包含的深层次和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最终促使社会矛盾化解才是维权新闻的最终目的。
引导理性思考而非煽动公共情绪。价值观念多元化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非是人人皆有稳定的价值观但存在群体差异,而是社会个体在各种价值观念充斥下的莫衷一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转型期社会充满了情感泡沫,放弃思考的看客心理和娱乐心理,以发泄情绪为目的的舆论暴力行为极易被引发。在社会极端事件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应该成为社会舆论的理性引导者,不应借报道社会极端事件进一步煽动公共情绪走向极端,而应成为公共情绪的引导者和理性灌输者,在坚持新闻操守的基础上对社会施以睿智和向上的影响。
总之,我国转型期社会的和谐发展有赖于一种弥合阶层、地区、性别、民族和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差别的社会整体观念的建构。新闻媒体应该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上解读社会极端事件,慎用 “以死抗争”等强调冲突的新闻框架,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中构建平等对话的渠道、提供理性思考的空间、编织连接不同利益群体的纽带。
扩展阅读
-
- 孙志军:文化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形成 2017-10-24 12:17:04
- 人民网评:舆论监督权岂容冒用滥用 2014-04-02 10:51:55
- 伦敦奥运报道网络媒体贡献巨大 2012-08-14 13:23:47
- 公共议题报道中意见呈现的框架分析 2012-05-07 10:56:41
- 滥用新闻自由是对新闻自由的最大侮辱 2011-08-05 10:13:12
- 论《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前后新闻报道的框架变化 2011-05-23 11:25:35
- 新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