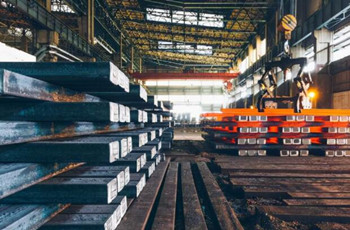诺奖得主的那些事:相当一部分不幸福,甚至痛苦

■毕星星
诺奖公布,有记者问莫言幸福吗?莫言笑而不答。不过我们从他以后的表现能感到他是幸福的。他不无得意地讲述了有人认出,有人追捧,收入排进富豪榜,一家人成为故乡宠儿等等奇遇,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
如果你读了陈为人的《摆脱不掉的争议——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一书,那么你会知道,不是所有的诺奖得主都是幸福的,起码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那么幸福的,有的甚至是非常苦痛的。
陈为人这本书列举了七位诺奖文学奖得主,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加缪,萨特,海明威,川端康成。他们获奖前后的写作和人生,对我们认识诺奖这个闪光诱人的桂冠,能提供更多方位的观察解读。
回头看,这几位的获奖经历,直叫是“成如容易却艰辛”,一个个都有崎岖坎坷的奋斗之路。在成名之前,他们都有和权力搏斗的惊险经历。成名之后,人生对抗并没有停止。诺奖百年,苦难纠结。这个世界级别的大奖,更多的和作家的苦难、国族的苦难、人类的苦难联系在一起。
俄罗斯三位获奖作家很典型。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出版以后,苏联官方将其定性为“反苏小说”展开批判。当局追索底稿,组织学生在作者住所前游行。获奖四日以后,当局就将其开除出苏联作协。特务密探包围了他,监视窃听无所不用其极。帕斯捷尔纳克为了免于驱逐出境,只好向瑞典文学院发电,声明放弃奖金,两年后在莫斯科郊外寓所孤独谢世。索尔仁尼琴的经历更加为世人熟知。获奖之前,他因为影射批评斯大林,被逮捕判处8年劳教,抨击苏联劳改营生活的小说发表,当局旋即命令作协开除了他的会籍。1970年获诺奖以后,特工如影随形全天候监视,一旦外出,立刻布控。《古拉格群岛》在国外出版以后,监控就变成了公开限制自由。直至将索尔仁尼琴逮捕驱逐出境。
如果说这两位属于开罪了当局受到迫害,肖洛霍夫不是,川端康成不是,萨特、海明威都不是。但是获奖以后,他们无论谁都没有摆脱巨大的精神苦痛。在获取诺奖问题上,肖洛霍夫和当局周旋有术,费尽心机,可谓遂了心愿。但这并不能逃脱苏联官方的重压,他背负着沉重的良心包袱不能自拔,依靠酗酒浇愁苟延。川端康成的自杀,有以为他是为警察头子竞选遭人诟病,痛悔自责。也有以为,从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到川端康成的自杀,显示的是日本文人极度悲观的人性。
萨特拒绝了诺奖,这当然是灵魂搏斗之后的隆重抉择。海明威举枪自尽,何尝不是果敢的自我了断。
在专制统治的世界里,诺奖作家为捍卫民主自由,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他们同样是从心灵到肉体锻炼灼烧。诺奖,始终萦绕着使命与权力,使命与灵魂的搏斗。诺奖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政治道义、历史真相和文化梦想基于一身,获奖之前,作家在为了普世的梦想苦斗。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成为一个背负理想的人,担当起民族和人类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而这些,不是每一个获奖作家都准备好了,也不是世俗的我们能想象周全的。
仅看幸福光鲜的一面是不够的。这就是谢泳教授在推荐陈为人这本书时说的:“欲了解诺贝尔奖的完整历程,本书开启了一扇特殊的窗口。”
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在全国上下欢呼莫言获奖,九霄之上洒下漫天鲜花的时候,提醒人们正确客观地了解诺奖,是非常必要的。诺奖不是毒药,却也不是化解一切难题的万应灵药。获奖之前,有或许艰难的道路走过,获奖之后,还是有或许艰难的难题要回答。世俗的幸福,不在诺奖得主的视野之内。
世人曾经把诺奖得主分为好多种,东方的西方的,诗人的纪实的,种族的语种的,我宁愿以世俗的眼光分为两种:“幸福的和不幸福的。”
扩展阅读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2019年国际扫盲奖获奖名单 2019-09-03 09:29:39
- 为什么是这五部长篇小说获奖? 2019-08-23 11:02:42
- 文艺评奖为何要“瘦身”? 2015-09-14 09:57:25
- 第二届文化产业 “金梧桐”奖评选启动 2014-10-29 10:12:01
- 解建军获奖感言:用现代方式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2014-05-13 14:26:46
- 莫言:诺奖奖金还囤着没花 2013-05-14 10:13:57
- 新闻排行榜